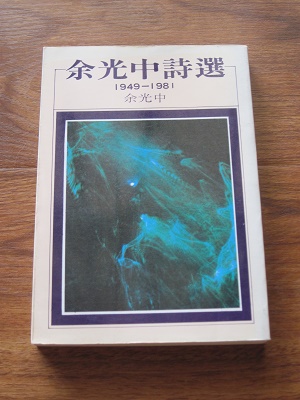上次读过他的《白玉苦瓜》,当时还蛮喜欢的。是70年到74年的作品。这次把年代拉长,看出余光中的成长轨迹。也才知道了,《白玉苦瓜》或许是他的巅峰期了。
49年,21岁,开始写诗。但是前面几年的作品比较受格律的条框捆绑。文字都僵硬。54年,26岁时,这首《咪咪的眼睛》多了一份灵动:
咪咪的眼睛是一对小鸟,
轻捷地拍着细长的睫毛,
一会儿飞远,一会儿飞近,
织织的翅膀扇个不停。
但它们最爱飞来我脸上,
默默脉脉地盘旋着下降,
在我的脸上久久地栖息,
不时一扑织织的柔羽。
直到我吻着了我的咪咪,
它们才合拢飞倦的双翼,
不再去空中飞,飞,飞,
只静静,静静地睡在窝里。
57年,29岁,这首《空宅》突破了字数一致的框架。更可贵的是,敏感的感官不再受限于事物表面:
电铃骤响,惊起了空宅的一头寂,
不住地摇尾,却又吠不出声。
没有熟悉的回答,没有手开门。
电铃响了,电铃的袅袅余音消灭。
电铃骤响,如投了枯井的一粒石,
没有廻波,没有反响。
齐竖的小耳朵,骚动的狂扑的小翅膀;
桌上的半身像惊得冻住了表情,
胆怯的钟忐忑着,如空宅的心。
电铃响了,电铃的袅袅余音消灭。
67年,不断尝试,出了一些佳作,有了自己的风格,像这首《或者所谓春天》:
或者所谓春天耶不过就在电话亭的那
厦门街的那边有一些蠢蠢的记忆的那边
航空信就从那里开始
眼睛就从那里忍受
邮戳邮戳邮戳
各种文字的打击
或者那许多秘密邮筒已忘记
围巾遮住大半个灵魂
流行了樱花流行感冒
总是这样子,四月来时先通知鼻子
回家,走同安街的巷子
或者在这座城里一泡真泡了十几个春天
不算春天的春天,泡了又泡
这件事,一想起就觉得好冤
或者所谓春天
最后也不过就是这样子:
一些受伤的记忆
一些欲望与灰尘
一股开胃的葱味从那边的厨房
然后是淡淡的油墨从一份晚报
报道郊区的华讯
或者所谓老教授不过是新来的讲师变成
讲师曾是新刮脸的学生
所谓一辈子也不过打那么半打领带
第一次 ,约会的那条
引她格格地发笑
或者毕业舞会的那条
换了婚礼的那条换了
或者浅绯的那条后来变成
变成深咖啡的这条,不放糖的咖啡
想起这也是一种分期的自缢,或者
不能算怎么残忍,除了有点窒息
或者所谓春天也只是一种清脆的标本
一张书签,曾是水仙或蝴蝶
书签在韦氏大字典里字典在图书馆的楼上
楼高四曾高过所有的暮色
楼怕高书怕旧书最怕有书签
好遥好远的春天,青岛
的春天,盖提斯堡
的春天,布谷满天
苹果花落得满地,四月,比鞋底更低
比蜂更高鸟更高,比内战内战的公墓墓上的草
而回想起来时也不见得就不像一生
所谓童年
所谓抗战
所谓高二
所谓大三
所谓蜜月,并非不月蚀
所谓贫穷,并非不美丽
所谓妻,曾是新娘
所谓新娘,曾是女友
所谓女友,曾非常害羞
所谓不成名以及成名
所谓朽以及不朽
或者所谓春天
到72年,顶峰期的《乡愁》和《白玉苦瓜》。
接下来,一直到81年,还像都循着以上两首的结构走。没有多大突破。
余光中还有一种类型的诗歌,就是怀古,咏古代诗人与古迹。屈原被颂了几次。这首78年,写于50岁的《漂给屈原》,我比较喜欢: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
有龙舟竞渡就有人击鼓
你恒在鼓声的前方引路
哀丽的水鬼啊你的漂魂
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
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
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
魂缠荇藻怎洗涤得清?
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
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已跃,所有的波涛
汀芷蒲兰流芳到现今
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
你流浪的诗族诗裔
涉沅済湘,渡更远的海峡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
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
你就在歌里,风里,水里
但是,以上这首《漂给屈原》就很明显的有余光中巅峰期的痕迹。从好一面来说,就是风格行成后,没人能取代。从坏的一面来说,就是没有突破了。我想,独树一帜,也要看高度吧。象余光中的自成一派,也没有能走向最高艺术殿堂,只能是小家了。
余光中著;洪范书店;民国七十年八月初版,民国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二版